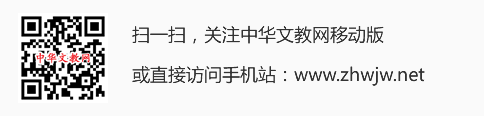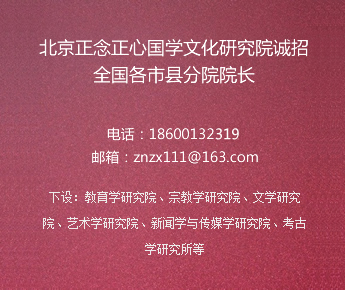同志加兄弟
——怀建邦
文/王克迅
2005年初夏,我回到阔别余年的故乡诸城,第一愿望就是去吊唁看望我的老战友——“同志加兄弟”苗建邦同志。建邦离开我们已三十年了,天人相隔,生死茫茫,但无时不在思念中。在市殡仪馆,我抚摩着他的骨灰盒,瞻望着他的遗容,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往事件件,涌上心头。
我与建邦是1947年相识的。这年春天,我从诸城城东区副区长岗位上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建邦也从昌城区调到县委工作组。当时我们只有二十岁上下(记得肩膀逼我小两三岁),县委机关还有几位与我们年纪相仿的同志,被称为“县委的一帮小孩”。在这帮小孩中,我俩的交往最多,关系最好。
1947年工作任务非常繁重,土改复查,支前,动员参军,镇反和组织农业生产等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整天忙于编辑《诸城通讯》,建邦一直在基层搞点,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每逢他到县上开会或汇报工作时,我们总是找机会叙谈。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多次在县委驻地路家道口村北的小苹果园里漫步交谈的情景。两个年轻人,一起谈工作,谈学习,也谈生活,更多的是谈理想,谈未来。当谈到各自的身世时,他说,他是贫民的儿子,几代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党领导革命,实行土地改革,才得到翻身解放。我则介绍,我是革命烈士的儿子,父亲1936年参加革命,在党领导下坚持抗战八年,积劳成疾,以身殉国。那时我们都是入党不久的新党员,能在县委机关工作,对党的培养和关怀无限感激。我们互相鼓励,互表决心,一定不辜负党的信任,忠于党,忠于人民,继承先烈遗志,坚持革命,革命到底,经得起各种考验,尤其是要经得起战争的考验。
1947年秋,国民党反动派以其二十个旅的兵力(另有数万土顽“还乡团”等反动地主武装),组成胶东兵团,发动所谓“九月攻势”,战火直逼诸城。
建国后,建邦长时间在区里担任一把手,当时他才二十岁出头。至今城西区吕标、谭家庄、七吉一带的群众,仍然记得他们年轻的“苗指导员”,身穿一件粗布衫衣,头戴一顶六角苇笠,挎一支二把匣子枪,骑一辆“大国防”,终日奔波于各村的情景。人们称赞他心地善良,态度和蔼,生活简朴,作风扎实,经常坐在贫下中农的炕头上,问寒问暖,同群众谈心,为群众排忧解难。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斗争坚决。在土地改革中,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同地主恶霸斗争。人们牢记,在反奸诉苦运动中,在谭家庄河滩上开公审大会,他站在桌子上,主持宣布枪毙西吕标恶霸张松山等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人心大快,感谢共产党为民除害,赞扬“苗政指”有水平,有气魄。
1950年秋,我因咯血到时驻胶县的滨北疗养院,不久,建邦也因肺部疾患来院诊治。我俩一起住在一处空闲的小独院里,三间房,一明两暗,我住在东间,他住在西间,朝夕相处近两个月。院方认为,我们有患肺结核的嫌疑,处于半隔离状态。那时,治疗肺结核尚无特效药,人们谈之色变,就像现在怕癌症一样。我俩同病相怜,互相安慰,相互鼓励,积极配合治疗。每天坚持到郊外散步,到城头呼吸新鲜空气,一起学习,读报,海阔天空地聊天,有时也开开玩笑,打打闹闹。建邦为人非常谦虚,有点内向,甚至有些腼腆有时见人还会脸红,特别是见到不熟识的女同志,为此,有的女病友故意地取笑他。他面目姣好,举止文静,我曾开玩笑说:你应该当个女孩子,该不是投错胎了吧?他红红脸,吃吃地笑了。当时物资供应比较紧张,病中所需营养跟不上。记得我母亲派我弟弟从故乡送来两只母鸡和一部分鸡蛋,我们便自己动手,杀鸡、煮蛋,分而食之,共同感受母亲的温馨。年底前,我先出院,回到地委宣传部,不久,他也出院回诸城。后来,我们多次回忆起这段“患难之交”,沉浸在浓浓的友谊中。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同志复出,经过整顿,全国的混乱局面有所好转。1974年初冬,我奉调参加了省委派驻昌潍地区工作组,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面整顿”的26号文件,期间,我多次到诸城,差不多每次都同建邦会面。老友劫后重逢,有多少知心话要说啊!记得有一晚上,在他住处的炕头上(那是他住在后营巷一个小院里),我们有一次长谈,谈当时的形式,谈“文革”中互相的遭遇。当谈到许多老同志仍然没得到“解放”时,为之叹息,鸣不平;当谈到有的老战友被迫害致死时,相互掩面而泣。他作为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人,“文革”中受冲击很厉害,身心都受到摧残,但他对党始终未丧失信心,对自己的遭遇处之泰然,一再说:“连国家主席都遭难了,何况我们呢!”
建邦同志曾担任过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他公道,正派,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爱护干部,关心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一位合格称职的党务工作者。记得有一次我出差到诸城,去烈士陵园凭吊,在烈士英名录上,未发现同我一起在城东区工作过,1947年牺牲在敌人刺刀下的辛公修通知的名字。我同建邦谈起此事,他说,按照规定,烈士分别由所在原籍县市管理,老辛是日照县人,可能原籍有他的档案吧?尽管如此,建邦仍不放心,立即派两名干部奔赴日照查询,结果发现因战争年代信息阻滞,辛公修同志的烈士待遇竟被漏掉了。建邦亲自向日照县委组织部提供证明,将公修同志的英名连同他画像,一起安放于烈士纪念堂。
文化大革命后期,诸城市郝戈庄公社贾戈庄村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入党,曾任过县农救会不脱产的副会长的老支部书记写信给我,说他在文革中被开除党籍,因派性作怪一直没得到改正。我想有关方面反映情况,但也迟迟得不到解决。后来我写信给建邦,在他直接过问下,问题很快得到解决。2003年这位90高龄的老党员病危弥留之际,仍眼含热泪,念念不忘党的关怀。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正像我国杰出诗人臧克家在著名诗篇《有的人》中的所写的,英年早逝的建邦同志,将永远活在乡亲们的心里。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对敌斗争坚定勇敢的青年共产党员;不会忘记这位心里装着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扎扎实实为人民服务的年轻区委书记;不会忘记这位公道正派,具有坚强党性的党务工作者;不会忘记这位对党忠诚,为革命勤勤恳恳,奋斗终生的好党员,好干部!
可以告慰建邦同志的是:他为之付出了全部心血的党和人民的事业,正如日中天,昌盛繁荣,从胜利走向胜利。还可以告慰的是,他的子女们,都能继承父志,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不断前进,事业有成。建邦,你应当含笑九泉了,我的好同志,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