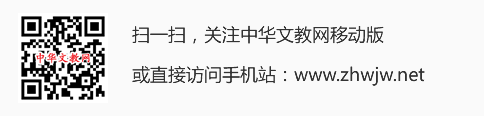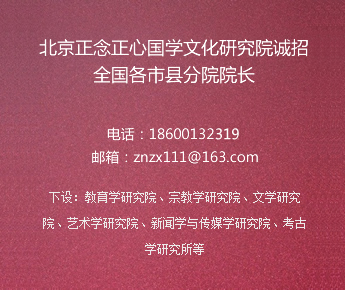我思、我感、我悟
——中国新闻史课堂上的些许思考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鑫
近两个月的中国新闻史课堂上,从周老师赋有逻辑和思想的课堂内容中,我学习、见识到了很多,对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除了对新闻史的学习外,在课余时间,我还查阅了相关资料,我结合课堂内容和老师的观点,对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及新闻史的研究,有一些思考和感悟。
我对中国新闻史这门课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课程内容,另一是当代我们怎样能更好地结合现代社会思潮研究中国新闻史。
首先,有关课堂内容方面。周老师在讲课中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值得深究的问题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对课程内容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此,我主要想谈谈我对章士钊新闻自由思想的所想所感。
章士钊出生在湖南长沙,其父章锦是乡里的里正,也是当地有名气的中医。章士钊自幼跟随其兄章士瑛受教,和父亲的接触不多。后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非法侵入,清政府却一再妥协,机器了民间运动的兴起。湖南是革命热情最高涨的地区之一,因此,章士钊在年轻时就有了非常强烈的革命抱负。
章士钊22岁时出任《苏报》主编,积极为革命宣传奔走,后因老师俞明震的保护,有幸躲过牢狱之灾,但由此更加激发了他的革命斗志。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章士钊考入东京正则学院,同盟会多次向他伸出橄榄枝,但被他拒绝。随后,他进入英国爱伯丁大学攻读逻辑学和政治经济学,这次规范而系统的教育形成了章士钊的“理性”思维方式。1911年他受孙中山先生所托回国。四年里,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给章士钊以非常深刻的影响,尤其是英国早期自由主义。章士钊的成长环境、三次赴欧经历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磨砺,都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有柳宗元朴素唯物主义和墨子的“兼爱”、“非攻”观念。章士钊继承和发扬了柳宗元行文的逻辑特色,墨子的政治观念和注重逻辑形成了章氏的思维方式。
1644年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写道:“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新闻自由是与近代社会的自由和民主等进步观念紧密相连的。一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随着传教士在华办报,新闻自由的观念才逐渐传入中国,由此迎来了中国第一次自由主义思潮。在这一浪潮中,章士钊的新闻自由思想别具一格。
总体来看,章士钊的新闻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第一,新闻事业观。章士钊认为新闻事业是为了“劣官稗政时见表爆,民间疾苦勤为宣泄,要闻之确捷又恒为他报先,社说栏中有领导社会政治之论。”新闻事业的功能是社会家督、维护民众、发表消息以及引导舆论,对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新闻事业做出了较完善的总结。章士钊还认为新闻舆论监督是必要的,“垄断天下之舆论而君者,久之他派尽失其自受之域。”舆论专制必将导致民心尽失,不能通过新闻行业来控制舆论,从而达到其罪恶的秘密。他反对政党之间的舆论霸权,把挟党见以排斥异己的行为称为“暴民专制”或“舆论专制”。第二,新闻业务观。章士钊对新闻的定义抓住了新闻的两个要素,即“新闻的本质是事实”,新闻应具有时效性,且新闻是代表正义的力量,是极具目的性的。章士钊主编的报刊,都有“通信”一栏,“通信”的名称先后有所不同,如《苏报》时称“舆论商榷”;《独立周报》时亦称“投通信”。他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与他“公理的世界观”和“新闻自由”主张有关。第三,新闻自由观。1644年,英国思想家约翰·弥尔顿首先提出了“出版自由”口号,一百多年后出现了“言论自由”,即公民有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表达意见的自由。章士钊一贯主张的“新闻自由”其实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总称。即“凡人可以自由发表其意见,不受国家之检阅也。无论何人可以任意出版,无需国家之特许也。”
在新闻自由的浪潮中,章士钊的新闻自由思想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这和他三次留学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章士钊新闻自由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西方早期自由主义,最开始推崇完全的新闻自由,但是也带有保守主义的痕迹;其次章士钊新闻自由思想较为明显的特点就是注重自由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以法律来界定自由的边界。章士钊一生中三次赴欧考察,其中在英国留学近五年,西方的近代自由思想主义对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章士钊认为,现有法规对自由只有钳制作用。各种法律的出台只是为了控制新闻自由的实现,检查制、保押费都是极其不合理的。而梁启超则强调只有将立法保障和自觉守法的自由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自由;自由必须和公理联系在一起,才有理性的自由。经过时间的检验,证明后者的理论更为贴近生活、正确可靠。但是不管章士钊对于自由和法律的判断是否正确,在当时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
章士钊的新闻自由思想有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其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对“哪里才是新闻自由的边界”这一问题的理解,这一观点的转变以解放战争胜利为界。最开始的时候,他认为“言论自由者,乃为凡人可以自由发表其意见,不受国家之检阅者”,强调“完全的自由”。但1946年以后,他又认为大陆法系指区别自由,给予限制,与英美之完全放任者不同。章士钊的自由观随社会形势发展而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章士钊新闻自由思想的功利色彩,也就是其政治性。他的新闻自由思想是为其“革命者”和“政治家”的身份服务的,因此会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
在章士钊看来,新闻自由的理念是一种“武器”。他强烈呼吁中国有志之士应当崛然奋起,排除艰难险阻,建设中国自己强大的新闻事业。“今一旦崛起,求侧足于大国之林,必使世界之毁誉易失其实,不惹世界之狂赞,即受世界之辱骂,可断言也。”
我认为,章士钊是中国近代集毁誉于一身的人,褒者誉之,贬者毁之,均穷形尽相,不遗余力。但是章士钊对我国新闻事业有着重大贡献,他准确捕捉到与新闻自由联系最紧密的要素——报律(新闻法),并且以审视“法”。透过章士钊可以看到近代早期的自由主义者是如何战斗的,同时反映了近代新闻自由观念的局限性。但是,由种种历史现象可以看出新闻自由思想实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并且呈螺旋状上升,而章士钊的新闻自由思想是新闻自由史上独特的一环。章士钊向国人积极介绍西方自由思想,尤其是英国的“完全的自由”,引导了强烈废除报律的呼声。他对新闻自由思想的引进和介绍,客观上起到了教导公众的作用,促使人们重新发现并积极思考自由的意义。
对于章士钊的一生,正如近代中国的历史一样,经历了无数的跌宕起伏,毁誉参半。他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分子,但我们不能否认他在将诶少西方自由主义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作为最早将新闻自由思想引入中国的报人之一,他的新闻自由思想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强调绝对的自由,和报律针锋相对,对还原当时社会的新闻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其次,有关课堂学习方面。在当今中国新闻传媒业迅猛发展以及业界对新闻专业毕业生“职业化”呼声日渐高涨的情势之下,大学生对史学方面的研究学习兴趣相比较从前有所回落。听了周老师的课,让原本觉得有些枯燥的史学类的课程,有了新的生机。我觉得原因归结于两点:一、周老师的课并不像一般史学课一样只停留在复述历史,而是在介绍历史进程中加以分析,并提出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供我们思考、讨论。这样的方式不仅完成了课程内容,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留出了自己思考的空间,使我们由完完全全的听众转变成有“权利”独立思考的课堂主人。二、周老师在授课过程中联系实际,并将自己的独特观点以别具一格的语言为我们进行剖析。中国新闻史对我们的学习及日后的工作发展而言有重要作用,也许它不能给我们带来直接明了的业绩,但这是一种积淀,一种作为新闻人的素养。著名艺术家马友友曾讲过,12岁到22岁这段时间.是一个人建立自己的“精神账户”的时间.以后一辈子都要在这个账户上“提款”。诚然,中国新闻史带给我们的正是“精神账户”的财富。将尘封的历史和正在进行的现实联系在一起,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认识现在,改造未来。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新闻业务方面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但我认为,新闻史,尤其是中国新闻史,更应该成为我们学习的基础和重点,这应该成为我们积累人文素养和新闻素养的关键环节。大家每每提及新闻史都会觉得枯燥、乏味,但如果通过改变相应的研究、教学方法,我认为是可以激发大家对新闻史研究的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