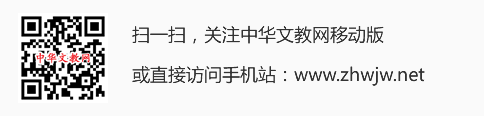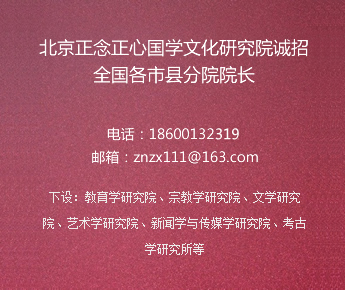急切
我后来想,他和她,兴许正是大时代下的我和你。
他是最后一位男嘉宾。
出场才艺是模仿M.J.的《dangerous》,细心的他甚至为自己添置了一套相当逼真的行头,黑色宽檐帽、铮亮皮鞋、白色衬衫搭配小西装——后来,在主持人的追问下,老实的他坦诚交待全身上下均出自淘宝,要400多块钱,但是他相信,“这笔投资一定是值得的!”——可问题是,他的舞蹈实在不堪目睹,而歌艺则更为糟糕,以至于我暗自庆幸这是本省的电视台,否则,被我那些北方的同学看到,必定会呵呵地讪笑起来,哈,浙江小男人!
随后是一段自我介绍的VCR,在迫不及待地介绍完自家的沿街店面及旧街区里一套住房后,他说,自己穿鞋后的身高是一米七——像《志明与春娇》中余文乐回应杨千嬅年龄质的那句“但是,我比你高”,有退避后的自信。——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他居然还是一位英文老师。
果不其然,其中一位女嘉宾提出了让他当场作一番英文自我介绍的要求。“没问题!”他回答得铿锵有力——我心想,阿叔,你拍戏吧!——并不意外,他的自我介绍又引发了全场新一轮欢笑,以至心直口快的女嘉宾当即表示,郊区英语啊。
随节目推进,他的人生背景渐渐展现:三十出头,县城户口,婚后离异,前妻在领证5个月后难以忍受他的无主见(或许有更为实际的原因)而离开,有父母无子女。
而此时,全场可怜巴巴地只剩下了一盏灯。主持人试图询问她中意他的原因,而令人咋舌的是,她居然当众哭了出来,泪水瞬间挂满脸庞,她哽咽说——
“我真的好想结婚嫁人,我真的好想结婚嫁人,我受了太多别人不堪忍受的伤,我真的好想结婚嫁人。”
难过
比遗失校园卡更麻烦的事情是补办,确切地说是,我又不得不面对她,这位絮絮叨叨的财务处阿姨。
扪心自问,我也能理解她的心境,作为机关的职工,不像其他教学或者学生工作的老师,整日有学生围绕身边,借以消磨时间,唯有办公室内三两位同事相处作伴。因此,每一回补办校园卡,她喊住我大诉家常,我也觉得情有可原,笑脸相迎。
可问题是,她每次都将我当作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一而再地重复相同的寒暄,事实上,大学两年多了,我至少补办了五张校园卡。
所以,这一回,我决定不再扮乖乖牌,我打算恶毒地在进门之时一口气告诉她,我的兆字是我爸爸取的也没有赋予特别的含义,我知道你家里也有一兆字辈是你家老爷子取的哥哥叫谭兆辉在美国念书弟弟谭兆锦在北京工作,真的,我都知道,我都知道。
同往常大同小异,今天,校园卡办公室只有两名职工,另一位年轻的小姐陶醉地传着短信,她则裹着厚厚的羽绒,低着头,有的没的翻杂志,像在想些什么。进门的瞬间,我决定,还是装死吧。
在递上学生证的同时,我几乎准备好了附上笑脸,回答她又一次的“咦,你的兆字是排辈分的吗?”的问题。可这一回,她扫过学生证上我的名字,却什么也没提,只是友善地提醒我,下次不要再弄丢了,她的声音轻得有些单薄,眼神有些暗淡,而气场更弱得仿佛只剩一格电量。这一回补办的过程史无前例地短暂。
看得出来,今天她有些难过。